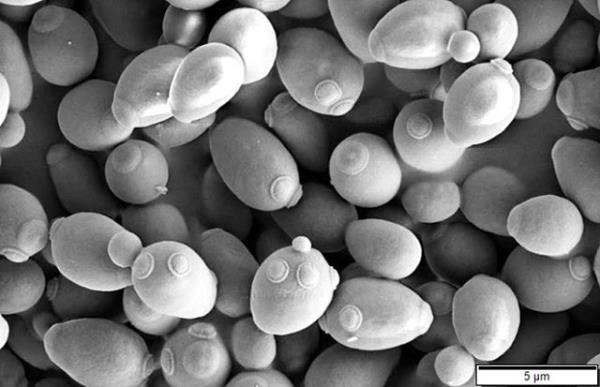1860年7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读者第一次看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自然选择理论。《达尔文论物种起源》(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是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撰写的三篇关于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著作的论文中的第一篇,它引发了大量回信,有些人很感兴趣,有些人则感到愤慨。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似乎对阅读格雷的经历记忆犹新,并在几十年后暗示了这一点。在他的文章发表150年后,他的文章在这个网站上的读者数量激增。
格雷是一位学者和博物学家,他摆出一副读者对达尔文的观点感到不安的姿态。他的文章开头写道:“对大多数人来说,新奇的东西是诱人的,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只是令人讨厌。”“我们执着于一个长期被接受的理论,就像我们执着于一套旧衣服……新观念和新风格让我们担心。”
这是一个诡计。格雷是达尔文为数不多的几个心腹之一,他为达尔文预先提出了自然选择的概念,他为达尔文提供了关于植物分布的关键研究。多年来,达尔文一直担心《物种起源》的出版会引发一场大灾难,而在美国,有一个反对者在众人面前若隐若现:路易斯·阿加西。
当时,这位瑞士出生的动物学家是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交换了理论;亨利·大卫·梭罗送给他一只瓦尔登湖的海龟标本;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这本杂志上对他赞不绝口。阿加西是格雷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在巡回演讲中很受欢迎,在演讲中,他展示了一种民粹主义版本的科学,这激怒了格雷,后者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精确的经验主义者。(格雷在给达尔文的信中暗笑道,阿加西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关于冰川的文章“不会让你大脑紧张”。)阿加西斯宣扬这样一种信念,即上帝创造的物种是按照它们确切的地理位置和等级划分的,在那里它们保持不变。这种反进化论的观点最终毁了他的遗产,但在1860年,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可以在达尔文主义到达美国的那一刻把它踩在脚上。
格雷在《大西洋月刊》上并没有维持他那勉强的伎俩太久。在他的第一篇文章结束时,他已经克服了他对自然选择的公开疑虑。传记作家Christoph Irmscher指出,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开始利用他的教授同事的观点来反对他。阿加西——“我们伟大的zoölogist,”格雷用鼻子嗅了嗅——观察到早期的物种包含了在后来的动物身上分别出现的综合特征。他称它们为“先知预表”。例如,灭绝的“类爬行动物的鱼”似乎预示着普通鱼类和爬行动物的出现。格雷大声问道:难道自然选择不是比他自己毫无根据的假设更能解释阿加西的观察结果吗?“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预言,”格雷继续说,“我们就不必奇怪,有些人在阿加西斯的书中读到这些预言,会在达尔文的书中读到它们的实现。”
《起源》出版后,达尔文赠送了一本给阿加西,并附上一张纸条,发誓他送这本书不是为了挑衅。阿加西似乎吓得说不出话来;尽管他在书的边缘写了愤怒的注释(“这真是骇人听闻”),但据信他读到一半就停止了阅读。尽管如此,他还是忍受了足够多的自然选择,以至于他认为自己陷入了一场混乱之中。“如果物种根本不存在,”他认为达尔文理论的结论是,“那么它们怎么会变化呢?”如果个体单独存在,”他在格雷引用的一篇评论中继续说道,“在个体之间观察到的差异如何能证明物种的可变性呢?”
“这是一个巧妙的两难选择,”格雷承认道,然后把矛头转向了对手。阿加西坚持认为,物种是上帝建立的“思想范畴”。格雷回答说,即使这是真的,这也很难阻止这些类别的变化——上帝的思想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变化和多样性。阿加西提出的这些“思想范畴”究竟是什么?“达尔文先生会暗示,整个争论所依据的分类哲学,就像他自己的学说一样,是纯粹的假设,很少被接受,”格雷写道。
换句话说,格雷认为,阿加西对神圣分割的宇宙的看法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猜想;他或多或少是在胡编乱造。对此,格雷提交了经过全面研究和细致论证的《物种起源》。阿加西,美国科学界的元老,突然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不科学。
阿加西只能重复他的信念,更强调,但不那么令人信服。他在剑桥失去了盟友,在科学组织中受到了批评。达尔文主义在他的学生中传播开来。1864年,阿加西和格雷在火车上交谈;阿加西宣称,格雷“不是绅士!”据传其中一人向另一人提出决斗。阿加西最后去了巴西做研究。“阿加西的朋友们很清楚,”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在《形而上学俱乐部》(The metaphysical Club)中写道,“对他来说,离开这个城市可能确实是个好主意。”
格雷的文章中潜藏着第二条攻击线,从我们的有利位置来看,这条线可能更为致命。阿加西认为,种族是分开创造的,和动物一样不可改变,上帝把白人放在最上面。达尔文传记作者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指出,尽管他反对奴隶制,但他的著作“为那些决心捍卫奴隶制的人提供了科学权威”。和达尔文一样反对奴隶制的格雷对阿加西的伪科学种族主义进行了抨击。“退后的第一步使黑人和霍屯督人成为我们的血缘关系,”格雷在谈到达尔文的血统理论所暗示的人类血统分支时写道。“这不是理性或圣经所反对的,尽管骄傲可能会反对。”格雷的意思是,如果人类来自一个共同的起源,那么也许某个动物学家和那些让他反感的黑人之间的联系比这位动物学家愿意相信的要紧密得多。人们可以想象,格雷写这句关于“骄傲”的台词时,阿加西斯的反应是多么的震惊。
阿加西对进化论的抵制削弱了他生前的名声,但他死后的种族主义却注定了他的名声。他的名字已经从学校和自然地标上删除;瑞士城镇面临着重新命名阿加斯中山的呼声。但在1860年,这些都是未来的事。在格雷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大西洋月刊》的编辑领导层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阿加西;他晚年还经常给杂志投稿。在美国人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斗争中,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科学的未来的斗争中,胜利者阿萨·格雷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些页面上。
为您推荐:
- 欧洲是极右翼势力的奴隶——这是所谓温和派绥靖政策的结果 2024-09-18
- 在亚马逊Prime会员大交易日之前,这些相机交易还能变得更好吗? 2024-09-18
- 关于深海生物的50个事实 2024-09-18
- 迪士尼解决网络纠纷的DirecTV将在签署新的长期协议后,于周六恢复服务 2024-09-18
- 钢人队的防守帮助贾斯汀·菲尔兹和进攻以2比0的开局战胜掘金 2024-09-18
- 在美国民意调查之前,特朗普第二次被暗杀的5个要点 2024-09-18